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英俊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莫言在2017、2018年井喷式发表了一批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作品。诺奖之后,莫言的创作心态如何?这些作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5月16日上午,2019首届吕梁文学季“莫言研讨会:诺奖之后的莫言”在贾樟柯母校山西汾阳中学召开,文学界对莫言的关注从获奖话题逐渐转向作品本身。正如首届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诗人欧阳江河所说,“莫言获得诺奖时才57岁,写作生涯还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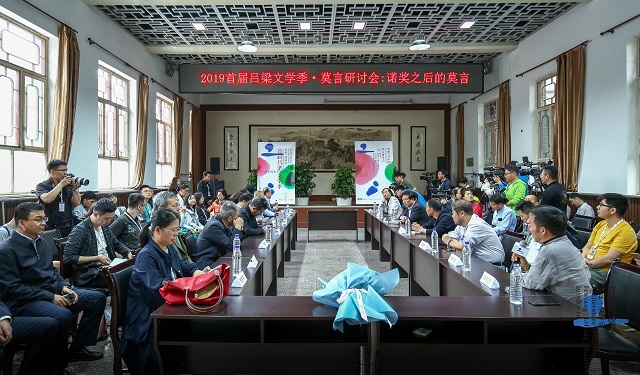
首届吕梁文学季莫言研讨会现场

莫言在首届吕梁文学季莫言研讨会现场
头顶桂冠,身披枷锁
“诺奖之后的莫言”自然成为与会者发言的焦点。“一个‘头顶桂冠,身披枷锁’的人”,作家苏童这样评价诺奖之后的莫言,“他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把那只手从枷锁里探出来,要把这个枷锁打碎,要把桂冠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带来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所以很多感受莫言有,我们没有,我们只能够设身处地去想象,想象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写作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容易的还有对作家自身局限性的超越。首届吕梁文学奖年度小说奖获得者梁晓声说,每一个作家都想要超越,但其实“超越是很难的”,“我们读李白的诗,读得多了,也会发现,气韵都是相似的。我觉得,努力、认真地写作,保持心态平常,就是可敬的。”
尽管莫言面临着这样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处境,但很多评论家还是对诺奖之后莫言的创作表示肯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从2017年开始,莫言恢复了活跃的创作,他依然保持着对此时此刻的中国现实生活、对此时此刻复杂经验的高度敏感。在评论家王尧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把莫言压垮,“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激活了他”。
也有评论家注意到了莫言在诺奖之后的改变——“平静、内敛、节制”。“莫言的力道还在那里,他的近作,与其说不露锋芒,不如说更加内敛、节制。他能说出中国乡村的故事,以他特有的方式和特有的真实”,评论家陈晓明说。评论家谢有顺也从莫言近作中感受到“他比以前更加平静,明显显得更加宽阔”。他认为,莫言之前的写作是热闹、狂放、喧嚣的,迫不及待,有很多话要表达。诺奖之后,他的写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迹象,里面有一种平静感。他的写作,包括他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变得节制与平静。
从乡村出发,写故乡人事
“新文学是从哪儿出发的?看上去是从北京大学、从大城市展开的新文学运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是从乡村出发的。”批评家张清华认为“从乡村出发的写作”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它不只是此次吕梁文学季的一个主题,它应该也是新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中国是农业社会,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学家们很少写乡村,写田园诗时才会写到乡村,几乎没有小说写乡村。新文学推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是世界文学,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世界视野后重新发现了乡村。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其实就是乡村,他写得最生动最重要的那些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都是乡村人物。
“莫言也是从乡村出发的,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从乡村出发的一个代表性作家。”
张清华认为,莫言身上和他的文字当中一直负载着家乡,他是从家乡走出来的,负载着家乡的全部信息,负载着中国农业社会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部信息,走向了读者,走向了世界。而评论家王春林认为,“莫言对故乡人事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鲁迅先生致敬,是在向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启蒙传统致敬。”
现在,乡村题材依然是莫言关注、书写的主题。莫言获奖之后的作品,以回忆故乡往事为主,与当下若即若离。陈晓明从细部切入小说文本,《地主的眼神》描写阶级斗争进入乡村后发生的矛盾,凸显的是人世与人心,篇幅虽短,但小说的时间跨度、历史感以及内在张力十足,尤其是那种朴实的乡土味、生活味,淳厚,意味深长。《斗士》可以看出莫言一贯擅长表现出来的执拗的性格,乡村邻里的恩恩怨怨和故事里的蹊跷被描述得淋漓尽致。《左镰》是一篇力透纸背的小说,力道在不经意间闪现。陈晓明说,研讨这些文本,是理解莫言、当代文学重建、当下乡土中国的一种视角。
王尧也认为莫言近些年的创作其实从未中断过和故乡的联系。从其近作《故乡人事》和其他作品来看,莫言重新赋予了乡村斑驳陆离的生活和人文结构以意义,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按照传统话语权力的对立模式,也不是一种立于都市对乡愁的缅怀。莫言能把乡土世界中人文结构的复杂性寻找、呈现、还原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首届吕梁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获得者王笛注意到,莫言的作品关注乡村,书写的是乡村的历史和革命年代、改革年代疾风骤雨的命运变迁。写历史的人,很容易受到历史的局限,文学家通过他的眼睛,通过他的思考,所展示的那种社会、文化、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本,为历史学家了解过去、了解中国乡村、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王笛认为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界要讨论的,历史学界也需要深入讨论。
文体丰富,更倾向戏剧创作
莫言近年来的创作包括戏曲剧本《锦衣》和组诗《七星曜我》(《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小说《天下太平》(《人民文学》2017年11期)、《故乡人事》(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三个短篇,《收获》2017年第5期)、小说《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花城》2018年第1期)、小说《等待摩西》和诗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飞翔》《谁舍得死》(《十月》2018年第1期)、歌剧《高粱酒》(《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歌剧《檀香刑》(《十月》2018年第4期,与李云涛合作)等,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
莫言近来创作的小说与他过去长篇小说铺陈狂放的风格相距甚远,与他过去的中篇小说内力张狂也有所区分。莫言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讲奇人异事,颇有古代笔记小说的影子。而近期发表的笔记小说,故事非常简短,也颇有古意。陈晓明说,莫言的写法内敛、含蓄,风格趋向于写实,文字极为朴素。戏剧性既是文学内在性机制的活跃因素,也是文学把握生活丰富性和广阔性的外向视野,而莫言小说深得戏剧旨趣,不管是场面还是细节,处处透着表演性。莫言擅长从中国民间艺术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也借鉴世界优秀文学艺术经验,这形成了他内涵丰富、有张力的表现方法。
谢有顺说,莫言既吸纳了新文学的要素,又接受了古代戏曲和小说元素,比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比如很多民间的说书作品,“他其实是把新文学的传统扩大了的作家”,恰恰是对新文学传统的扩大,成为今天莫言写作受到世界关注的重要原因。张清华和王尧也将莫言的笔记体小说创作看成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关系的意愿表达或者是对于人文传统的恢复。他们认为,莫言通过自己的想象,试图把笔记体这样一种小说文体重新激活,过去莫言和民间的文化联系更多,但是现在似乎又多了一个维度,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和传统的文人之间建立起联系来。
关于莫言的诗歌,评论家们认为,莫言诗歌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叙事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并且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雨中散步的猛虎》等诗歌看似是率性之作,但确实是写眼中所见、心中所想,貌似脱口而出,看似杂乱无序,却又妙语连珠,所谓诗性或者诗句的关联逻辑走的都是点石成金和随机应变的险棋。
评论家们把目光更多放在了戏剧上。陈晓明认为,《锦衣》这部戏剧作品元素丰富,莫言深谙中国民间戏剧的门道,兼通欧洲戏剧之精要。莫言以小说笔法入戏剧,由人物性格带动情节发展,显示了莫言将小说与戏剧两种艺术杂糅交合的艺术才能。戏剧剧本《高粱酒》对原小说作了较大改动,基本格局未变,于占鳌多了一点滑稽色彩,戏剧性和表演性因素都十分充足。王春林认为民间化是莫言戏剧的重要特点,尤其是《锦衣》。他认为当代文学史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去戏剧化,从这个意义出发,莫言坚持写戏剧,首先有一种文体平等的意义。虽然形式上是借助了戏剧这样一种本土化、民间化的文学文体,但是它非常深刻地传达出了现代启蒙的精神价值立场和人道主义情怀。
在李敬泽看来,莫言选取戏剧这种文学形式,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艺术考量,莫言可能通过这样一种人间戏剧的路径重返文学现场,戏剧这种文体更有利于回到乡土,回到大地。
返乡:重构与超越
莫言诺奖之后的“返乡”意识似乎更加明显。这不只是世俗伦理上的亲情式的返乡,也是现实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返乡。张清华认为,当莫言回到故乡,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现实,因为现实不是盛大的“夹道欢迎”,现实是非常真实的日常生活,包括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每当他回到故乡,他就会找回这个现实。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李师东说,故乡是莫言的精神家园,他从中找到立足点,能够让自己沉下心来写作。实际上还是在重写自己的过去和认知。
“莫言在酝酿第二次革命。”苏童说,莫言进行了诗歌、戏剧、小说上的诸多尝试,他在重新摸索,再次出发。但乡村依然是莫言的根据地,依然是他精神的着迷点。谢有顺认为,莫言在观察、书写乡村的同时也试图在超越乡村。莫言是一个精神体量庞大的作家,他的近作体现出了他宽阔、庞杂的视野,他的整个精神气息也透露出来了。有了这种精神体量,才会有一种更大的格局。一个作家最终能否走得更远,主要取决于他是否有那种压抑不住的、能让人体察到的庄重之心,这份庄重之心会让作家将自己作为审判的对象、被观照的对象,写出大的作品,而且整个写作格局还会更大。莫言是有庄重之心的作家,诺奖之后,他也一直在谋划大的作品。
最后总结时,莫言说,一个作家所有的感受,实际上都来自于他的写作。一个作家如果在某个方面跌倒了,爬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用笔写作。莫言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英俊 摄影照片由吕梁文学季主办方提供)